“我也有勛章了,和電視里的一模一樣!”自從收到街道頒發(fā)的“光榮在黨50年”勛章后,姥爺逢人便夸。
姥爺76歲了,黨齡53年,退休前是北方重工集團的一名天車工,我從小在姥爺身邊長大,沒少聽他的故事,小時候聽不懂什么大道理,只記得他的一生總是離不開糧食。
40年代,姥爺出生于土右旗的一個普通農(nóng)村,在勉強上完初中后,他被家里逼迫著去供銷社上班,單純就為能有一頓飽飯。1963年,到了征兵年齡,姥爺義無反顧地去當兵,想的也是給家里減少一個人的口糧。部隊生活嚴肅艱苦,認真負責、積極進取的他先后擔任了班長、排長。1965年7月,表現(xiàn)優(yōu)異的他在部隊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
80年代的土右旗農(nóng)村,姥姥帶著三個孩子,身上肩負的不僅是養(yǎng)育孩子的艱辛,更是農(nóng)民賴以生存的生計。我后來聽媽媽說,多虧有在包頭上班的姥爺,在農(nóng)村的日子里沒有為糧食發(fā)過愁。被當做驢糞蛋的黑棗,連皮吃的栗子,這些農(nóng)村孩子從未見過的零嘴,像爆炸性新聞一樣傳滿整個村子。但是,在媽媽他們姐弟三看來,再稀罕的吃食都不如一頓白米飯讓人期待。姥爺說,計劃經(jīng)濟時期,糧食很難多出來。由于住單身宿舍,自己的伙食都在食堂解決,每次有吃不完的白米飯,他都會用報紙認真包起來,凍在室外或者食堂。到了周末,他便騎五個小時的自行車從包頭城里趕回土右旗的老家,把大包小包的吃食帶回去。
1986年,姥姥帶著三個孩子終于搬到了包頭市區(qū),結(jié)束了和姥爺?shù)膬傻厣?。姥姥三十多年的生活?jīng)驗,自然不會讓孩子們?nèi)甜嚢ゐI,但是全家只有一個勞動力,溫飽問題又提上了日程。說起這段故事,姥爺總會忍不住地提起街坊的糧油店老板。由于家庭困難,姥爺每次去買糧都是散稱,根本一次性買不起整袋的大米白面。做鄰居的日子長了,糧油店的老板便會主動給姥爺扛起一袋白面,“拿去吃,有錢了再給。”這也是姥爺因為糧食結(jié)交的第一位朋友。
再后來進入90年代,我也出生了,中國社會逐漸取消了計劃經(jīng)濟,姥爺依然堅守在車間里,為還沒結(jié)婚的兩個兒子奮斗著。在我小時候的記憶中,每天清晨,姥爺都會用開水沖泡一顆生雞蛋,再加上一些干貨,就成了一頓早餐。每次我都會好奇是那是什么味道,姥爺總是一副人間美味的樣子。長大之后的一天,我也如法炮制了一碗,發(fā)現(xiàn)味道真是令人堪憂,我才終于明白了姥爺對這個家庭的付出遠遠超過了我的想象。
今年是建黨一百周年,姥爺一生的故事讓我深深地認識到,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百年歷史也是一部中國糧食變遷史。在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領(lǐng)導(dǎo)下,中國人民擺脫了饑餓的威脅,真正解決了吃飯的問題。即便是在近年來國際上糧食危機頻發(fā)、糧食價格上漲,1億多人面臨嚴重的糧食安全危機,新冠肺炎的流行加劇了全球糧食安全危機的嚴重局勢下,中國人民仍能平靜安穩(wěn)、泰然處之。這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歷史上值得濃墨重彩書寫的炫麗華章。
飽食終日,粒粒可馨。如今我們都身處小康之年,姥爺已步入古稀,他的早餐里也再沒有那碗沖雞蛋了,每次有新鮮的吃食,我都會第一時間拿給他。姥爺?shù)囊簧缭搅诵轮袊總€歷史時期,見證了從“吃什么”到“怎么吃”。讓他總結(jié)過去,這位老黨員只會說一句耳熟能詳?shù)?ldquo;誰知盤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,我卻深深知道,每一粒糧食都是姥爺經(jīng)過歲月洗禮得到的,而這些珍貴的故事也教會了我一份對家的責任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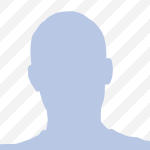







評論